经上海闸北区文化馆馆长周国成介绍,我得以拜识了“稚英画室”的传人——杭鸣时先生。杭鸣时承传父亲杭稚英的衣钵而又推动了粉画艺术的发展,成为当今画坛上的粉画巨子。踏进杭鸣时家,一块大匾“金粉世界”跃入眼帘。杭鸣时说:“此乃苏州书家卫东晨先生九十五岁时所写。”我不经意地说:“如写成‘金粉世家’则更好了。”杭鸣时说:“你说对了,卫先生了解了我的家世之后,在他百岁之时又欣然为我写了‘金粉世家’。”
杭稚英系中国月份牌画种的开创者之一。1921年,杭稚英首幅月份牌作品《闲游春阁》在沪面世,那端庄美丽、秀外慧中而又充满自信的女性美一下子吸引了社会大众,他也一举成名。1922年,杭稚英成立了“稚英画室”,事业日趋发达,画风也日臻成熟,求购其作品的客户络绎不绝,出版商也纷纷邀稿。鼎盛时期,一年竟创作了80张月份牌画。当时的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章炳麟先生得知其名,便录李太白“齐有倜傥生,鲁连特高妙。明月出海底,一朝开光曜。却秦振英声,后世仰末照。意轻千金赠,顾向平原笑。吾亦澹荡人,拂衣可同调。”古风诗一首赠之。
1937年,正当杭稚英事业走上巅峰之时,日寇占领了上海。日军为了宣传他们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,要杭稚英为他们画美人图。杭鸣时回忆说:“那时我虽小,却还记得一日本军官将20根‘大黄鱼’(十两一根的金条)放在桌上,诱逼父亲与他们合作,我父亲以有病不能提笔画画为由予以拒之。日本军官放话‘你既不能画画,以后在市面上也不希望看到你的作品’,说着便扬长而去。”靠稿费收入的杭稚英一下陷入了困境,四十来口人的大家庭怎么生活?无奈之下,他只得东拼西凑靠借债度日。家人只得靠吃面疙瘩、山芋过日子。其实,杭稚英的骨气在上海是早出了名的,记得20世纪30年代初,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60岁寿,他的弟子来找杭稚英,要他在景德镇瓷盘上绘制黄金荣的肖像。杭稚英坚辞不肯,但他深知自己这一举动得罪了地方上的恶势力,为了避灾,他只身逃往苏州,避了好一阵子风头。
8年的艰难,终于熬出了头,杭稚英盼来了抗战胜利,“稚英画室”重新开了张。他日夜拼搏,经2年的苦干,终于把8年来欠下的债还清,而他也因劳累过度而积劳成疾,落下了一身的毛病。
1947年,杭稚英在家养病时画下了他最后一幅尚未印刷的遗作《霸王别姬》。原作长74厘米,宽54厘米,它几乎浓缩了月份牌画作中西合璧的艺术精华,也浓缩了杭稚英一生追求艺术的心血。作品取材于杨小楼、梅兰芳合演的《霸王别姬》,整个画面一气呵成,色彩饱满鲜明,人物布景和谐协调。画面上霸王焦躁不安之神态表露无遗,而虞姬却文静柔美镇定自若,手捧项羽盔甲与霸王作别。杭稚英用擦笔水彩画法描绘了英雄与美女的姿态,而对项羽的头发、胡须以及铠甲则用了中国工笔画的技法。同样,虞姬的凤凰头饰、其手捧的头盔和衣裙上的万福刺绣图案都用了极其细腻的丝毛技法。至于背景如方砖、龙椅、地毯、龙柱、围幕皆丝丝入微,景景逼真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创新,大胆用喷笔调整,让项羽衣褶和背景的宫廷环境得到自然过渡,画面虚实有致,主次分明。杭鸣时回忆说:“父亲画完这幅画后已精疲力尽,不久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,享年仅46周岁。”
杭鸣时知道,这是父亲的绝笔,也是杭家的传家宝,故倍加珍惜。不料,“文革”来临,杭鸣时被抄了家,红卫兵把这幅画当做“四旧”抄了去,好在造反派中有几个学生知道此画是老师的珍爱,过了几个月,他们偷着将画还给了杭鸣时。1973年,“四人帮”在全国掀起批黑画的高潮,有人告密说杭鸣时家藏《霸王别姬》黑画,学校个别人以杭鸣时又要“蠢蠢欲动”为由打了小报告给省领导。谁料,省领导来检查时未作表态走了,此事也就草草收场,原画归还。直到1981年,杭稚英的《霸王别姬》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出,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据悉“稚英画室”已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向有关方面提出了申报,希望能申遗成功。
海宁政协编的《装潢艺术家杭穉英》买了三四年才买到,因为只是本印了一千册的内部资料,薄薄的110页,费去123元。一晚上读完远没有渴可解,所辑录的文章材料平平。最有趣的还是那个老段子。说是作为商业画家的杭穉英参加一美术界宴会,席间讨论色彩问题,杭穉英不禁参加讨论,一专画鱼的画家不客气地说了一句:“你也配谈色彩”,让正在拿汤匙挽汤的杭穉英一时僵在那里。
这段子是杭穉英的儿子杭鸣时讲的,道出了那时商业画家的尴尬处境。
已然是长兴老街的人民路上,一位名叫孙功安的画像店在这里已经开了20多年。从他的擦笔画中,我们看到了一种古典的文化,与发展迅速的照相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,擦笔画似乎离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远,与孙功安一同坚持的同行已寥寥无几。近日,记者再次来到这家画像店,与孙功安面对面地交流、采访。
“当时,自己经营画像店也是为了有工作,混口饭吃吃罢了。就像很多人从事木匠、泥匠工作一样,只不过,我从事的行业有点特殊罢了。”据了解,孙功安曾上杭州美校拜师学艺,到上海某画苑打工画广告。1990年,孙功安产生了办个画像店的念头,并在家学习擦笔画,3个月后掌握了擦笔画的基本技巧,并在人民路上摆起了画像摊。就这样,孙功安的擦笔画生涯从街头摆摊开始了。
“当时,接到第一单生意就赚到了35元。”孙功安一直兴奋了好几天,因为当时这个价让他很满足,普通老百姓打一天的小工才收取8~10元的工钱。
“擦笔画又称 ‘软笔画’,是我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之一,难度就在笔锋上,没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和基础是很难画好的。”孙功安说,以前学过素描,这为他画擦笔画奠定了基础,特别是在形与结构的把握上很到位。
“解放前,画像店多得是,如今在茫茫的大城市中很难找到一家像样的。”孙功安告诉记者,如今照相技术飞速发展,照相馆遍地开花,数码相机也走进千家万户,这对擦笔画的冲击很大,因此这门技艺也就渐行渐远了。
原本,孙功安以为自己的画像店会和其他的同行遭受一样的命运,但让孙功安想不到的是,他的生意并未受到影响,反而有些人愿意出高价钱让他画像。他的顾客群遍及长兴各地,甚至广德、江苏等周边地区也有人来请他画像。
为何先进的照相技术未能影响他的生意?孙功安给出了记者这样的解释:首先,有些老照片没法翻拍,用照相技术处理不了,像这些情况大多数人会求助画像店;其次,有些人认为画像挂在家里比较上档次,就像艺术品一样。
现在传统的画像师越来越少,这门传统技艺有日渐萧条之意。尽管如此,依然有人在为其执着地坚守着。
如今,相机已经走入千家万户,只需轻轻一按,一张画面就保存了下来。不过在相机没有被发明以及普及之时,人们想要留下自己的影像就需要去找画像师作画了。不过现在传统的画像师越来越少,这门传统技艺有日渐萧条之意。尽管如此,依然有人在为其执着地坚守着。
一幅幅逼真的半身素描画像,就如一张张老照片,散发着一种久远的气息。而它们的勾画者孙功安正端坐在画板前,静静地用炭笔描画着新的作品。只需要一张普通的黑白照片,他就能逼真地在纸上再现画中之人。“这个素描又叫炭笔素描,是起源于西方的,一般如果要画一张素描画的话,需要先构图,然后画好基本的线条结构,再填充内部的内容,最后就是进行阴影等一些处理,这是基本的素描步奏。”说话间,画纸上的人像已初现轮廓。
别看孙功安年纪不大,但是他从事画像这门手艺已经二十六年了。这二十六年间,他走过了初入门的青涩,登堂而未入室的煎熬,学有所成的喜悦。
技术的日益精进来源于自己不断的学习与锤炼。现在孙功安基本上只要两到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幅素描画像。不过他透露,其实自己只能算是半路出家:“我原先不是学这个的,但是我从小就喜欢画画,先自学,后来也跟了一些师傅。一开始是比较辛苦,后来等有了进步之后,每画完一张画心中都有一种喜悦感,就是这种喜悦感让我坚持了下来。”
坚持因为热爱,奋斗为了向前。除了炭笔素描之外,孙功安还自学了油画、山水画等多种类绘画方式。平常无事时,他就会坐在自己的店门口,专心致志地描绘画像。而他这样一种对画像艺术的执着爱好,也让附近的居民非常钦佩。“他画的画我很喜欢看的,而且我觉得他画得很逼真,很棒。我平时没事么也会和他聊聊,他人也很不错的。”隔壁的杨大爷提起孙功安便竖起了大拇指。
不过,随着摄影技术和电脑绘画的普及,画像的人越来越少了,而年轻人,又不愿意去学这种费时的画法。但孙功安认为,作为一项传统的工艺,画像有它存在的独特艺术意义与优势:“虽然现在电脑什么的都是很发达,但是电脑扫描出来的照片和炭笔绘画出来的还是有区别的,因为炭笔素描出来的艺术性更高,特别是对人身体脸部肌理纹路的还原等一些方面的艺术性,是电子产品这样的成像技术不能替代的。”
正是因为画像艺术这种独特而隽永的魅力,使得孙功安一直醉心于此。
孙功安说现在他的儿子在国外学习绘画艺术,他希望儿子将来回国之后,能将画像这门艺术一直传承下去。“因为我儿子是看我这样画像长大的,现在他也在外面学习绘画,所以我希望他回来之后能继续像我这样,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”
曾经风靡数十年、开创中国现代广告设计之河的上海滩“月份牌”美术作品,如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、一份珍贵的视觉文化遗产,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上海月份牌画展,一幅幅精彩的原始展品,将重现当年的迷人魅力。
起源于清末、辉煌于民国初期的上海月份牌广告画,因为有了郑曼陀(1888~1961)“擦笔水彩”的首创和杭穉英(1900—1947)等画家的发扬光大,再加上当时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推波助澜,这些独具上海滩风花雪月、花样年华风格,以及主题多样、老少皆宜的画作,一经推出便受到当时社会大众的广泛喜爱。尽管1949年前后开始将其打入低俗之列后难见踪影,但还是有不少作品能够流传至今,而且依然风采不衰、让人心驰神往,甚至在中国美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,足以说明它的艺术价值非同一般。
这段时间,南京博物院民国馆在举行老月份牌广告画展。画作者包括郑曼陀、徐咏青、杭穉英等名家,题材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山水画、吉祥图案等,也包括当时的城市新生活。画面上有传统古典美女,更有在苏州园林打高尔夫这样的摩登女子,月份牌画家究竟为什么会这么画,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,很让人好奇。
谁是月份牌画家代表人物? 人称“梅兰芳”的杭穉英
“侯老师对我们特别好!”
10月13日到临朐县蒋峪镇慧敏小学采访时,该校二年级学生侯继奎抢着对记者说。
“怎么个好法呢?”
“像妈妈一样。”侯学奎想了想说。
记者见到了侯学忠这位“像妈妈一样”的男老师。他中等个子,一脸憨厚的笑容。这位备受孩子们喜欢的独臂老师,自19岁开始教学,如今已在讲台上站了整整35年。
提升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教孩子
1979年夏侯学忠高中毕业时,适逢蒋峪镇侯家峪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退休,侯学忠便从他手中接过了接力棒,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侯学忠幼年时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左臂,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,一手拿课本,一手在黑板上写字。但如果一边板书一边回头看课本必然会影响讲课效率,他便提前将课本内容记熟,只拿一把尺子、一盒粉笔上讲台,讲课行云流水,效果出奇得好,学生们非常崇拜他。侯学忠刚到侯家峪小学时,全校共有一、二、三年级42名学生,他是该校唯一的一名老师,一周课时多达40节。虽然时间紧张,他仍然十分注意学习。他教的虽然是低年级学生,但却经常翻阅、学习初高中课程。他说:“提升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教孩子,只有掌握了更加丰富完备的知识,才能教出好学生。”
除了教好基本的语文、数学课程,侯学忠还经常指导孩子们绘画,这方面的“本领”也是他后来自学来的。为了开拓孩子们的视野,侯学忠决定学习绘画知识。1983年,他从书画杂志上找到一则擦笔画招生信息,急忙写信报了名,却被200多元的学费难住了,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十几元。为节省费用,侯学忠只订了擦笔画教材,自己用毛笔、棉花和海绵等材料制成擦笔刷使用。绘画时,他先用铅笔勾出浅浅轮廓,再用自制的擦笔刷轻轻涂抹,勤奋的练习让他不到一年时间就能画出惟妙惟肖的擦笔画。
被人需要也是一种幸福
2000年,侯家峪小学与慧敏爱心小学合并,侯学忠转为一名公办教师。学校师资力量薄弱,没有美术、书法、音乐等专业专职教师,侯学忠主动请缨担任艺术教师。他找来自己会唱的《东方红》、《歌唱祖国》等歌曲,一首首地分解简谱,自学音符和节奏,再对照学习新歌教给学生。校长王金志说:“像侯老师这样严格要求自己、竭尽所能的老师,既是学校的财富,也是学生们的福分。”他专门为侯学忠定制了画架、购买了雕塑用泥。去年,侯学忠安上了义肢。“现在方便多了,上课可以用手摁着纸,对照着给学生们示范了……”侯学忠充满了感激。
在侯家峪小学教学时,侯学忠既是校长,又是老师,还是学校的“敲钟人”。每天早上,他早早地赶到学校,打扫教室、办公室,等一切收拾妥当便站在校门口接学生。当时侯家峪小学条件简陋,没有现成的桌凳,侯学忠便和泥垒成垛子,再架上凹凸不平的长条木板当桌面。冬天,教室里没有取暖炉,他爬上爬下用一块块碎砖将窗户封严。为让学生喝上热水,他一人去水井里打水给学生烧水喝,这样危险的活他从不让学生帮忙。他用一根绳子一头拴住水桶,一头缠在自己的右臂上,用脚踩住绳子,拿右臂当辘轳缠上一圈又一圈地往上提水,有时还得借助牙咬住绳子。每提上一桶水,他的胳膊往往会被勒出一道道血印。
侯学忠平时上课任务重,白天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,只能利用晚上批改学生作业。过去村里没通电,本着“作业不过天”的信条,侯学忠就点着煤油灯批改作业,每天都到深夜,鼻窝、眼窝全落满了烟灰。侯家峪村的村民感叹道:“侯老师的煤油灯是我们村里的“长明灯”。看到侯老师的灯亮着,我们心里就暖烘烘的。”
即便是这样,侯学忠却不觉得累。他常说:“大家需要我,说明我活得有价值。被人需要也是一种幸福!”
每个学生都是心头的宝
在慧敏小学,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:下课时,学生们围着侯学忠有说有笑;上课时,学生们抢着举手回答侯学忠提出的问题。他和学生们的关系,既亲密又和谐。“家长把孩子交给咱,咱就得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们,每个孩子都是我心头的一块宝。”侯学忠对记者说。
10岁的王永杰生性好动,经常不吃午饭,下午饿了就吃零食。侯学忠怕他营养跟不上,每天靠着督促他吃好午饭。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,侯学忠不仅是老师,也是“妈妈”。二年级学生王立燕家里经济困难,父亲在外打工,妈妈瘫痪在床。有一次,班里收101元钱的课本费,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交上来,如果让她回家拿的话,这个女孩恐怕就不会来上学了,侯学忠默默地替她把钱垫上。1984年,当时上四年级的郎咸国因心脏病住院,自身家境困难的侯学忠硬是借了100元钱塞给郎咸国。郎咸国出院时落下了三四个月的课程,侯学忠每晚去给他补课,直至他跟上新课。像这样的事情,30多年来侯学忠不知做过多少。他帮学生买文具、垫付的资料费更是不计其数。侯学忠淡淡地说:“这些钱,自己还能勉强承受,也是当老师应该做的。只要学生们有出息,能为国家做点事,比什么都让我开心!”
炭相源于清朝,在中国民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顾名思义,即是用画笔沾着炭粉一笔一笔勾画出个人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。传统手绘的炭相不反光,质感细腻,在不受潮、没虫蛀的情况下,可保存100年不褪色。正因为这个特点,在近代广府地区,炭相主要用于保存故人的音容笑貌,成为后世追忆亲人的精神归属。早些年的广州大新路曾是炭相瓷相一条街,但今天只剩寥寥少数还在继续经营,其中六旬老艺人朱肇荣的“美的”相馆就是其中之一。
手绘炭相完美再现故人容颜
在各种五金店和布料店林立的广州大新路,朱肇荣师傅的“美的”相馆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这处外间仅4平方米的铺面摆放着各式炭相和瓷相,以黑白两色为主,在周围的纷繁色彩中显得别有一番沉静。
“这些炭相、瓷相都出自我手。”朱肇荣将手绘炭相与数码冲印照片并排悬挂在一起,对两者的优劣娓娓道来:“同样是放在玻璃镜框里,灯光照射下手绘炭相不反光,局部明暗对比分明,立体感强,放100年也不褪色;而现在的数码冲印成本低,速度快,但长时间保存容易变色,照片表面会发蓝。”
在采访期间,陆续有顾客带着故人照片上门,有的照片很小,仅仅一寸,朱肇荣问清尺寸要求后,会将照片扫描并放大,打印出来,对照着在炭化纸上进行手绘。“其实说白了就是工笔画法,只不过作画原料是炭精粉。”朱肇荣解释说,如今的美术学院也有工笔课程,但极少有人画工笔人物画,每根头发丝都得一遍遍细细加工。
由于炭精粉不像水彩颜料那么好上色,朱肇荣在打好草稿后,需要用毛笔蘸取炭精粉,在纸上一遍遍地刷扫,几十分钟后才缓慢勾勒出人物的大致轮廓。
有人想为几十年前的故人晒相,但现存的照片已经泛黄、残缺,这种情况数码冲印很难办到,但如果是手绘炭相就没问题。朱肇荣说:“我可以根据经验,加上咨询顾客,帮忙补上残缺的部分,最终让顾客觉得非常像,满意为止。”同样的,对没有保存故人照片的后代来说,对朱肇荣详细讲述故人的面貌特征,他也可以通过多次修改,完整呈现出顾客想要的模样,这叫“追像”。
十五岁就开始独立接单
朱肇荣是广州本地人,他的相馆是从父亲手里继承的,算起来已经营了七十多年。老一辈手艺人典型的家庭式传承方式有个好处,即能够在实践经验中千锤百炼。从小到大,朱肇荣没有接受过任何美术训练,全凭观察模仿父亲画画的手艺,再慢慢自己摸索。
新中国成立前,有一些炭相老师傅可以根据旧照片,在纸上打出九宫格,按比例直接下笔画。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晒相技术传入内地,无论顾客拿来的是照片还是胶卷底片,朱肇荣都能直接放大到要求的尺寸,这样对照着画,精确度也能提高不少。
“从十五岁开始,我就单独接单了。”朱肇荣坦言,那时候会画炭相是一门手艺,可以养家糊口。自己家的招牌在大新路的几家相馆中还算比较响亮,虽是少年工匠,生意也不错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人们一个月工资大概二三十元,一张炭相卖几毛钱,瓷相会贵一点,卖到一两块钱。
改革开放后,瓷相逐渐变得多彩起来,因此消费对象也不再局限,有人愿意为自己制作精美瓷相留念。但总体来看,无论是瓷相还是炭相,定做的人依然越来越少。朱肇荣无奈地说:“现在需求少了,画炭相专用的炭精粉也变难买了。”
可惜手艺无人继承
朱肇荣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许多广东乡下地区的客人都会闻名来到省城,找到“美的”相馆,要求制作炭相瓷相。那时乡下祖屋、祠堂数量多,照例需要挂祖先像,潮汕地区的客人喜欢16寸的炭相大照片,还有一些梅县地区,茂名、湛江的客人,也有客人是外出经商,回家探亲时经过广州,想着顺便带一两幅炭相回去的。
随着每年清明节到来,朱肇荣的炭相生意会稍微好转,但暂时繁盛的背后掩盖不了行业的落寞。朱肇荣表示,在数码照的冲击下,炭相已日渐式微,如今来做炭画像的人并不多,年轻人更少,主要还是回头客,有时候整整一个月也没几单生意。
炭相的实际功能已逐渐减弱,如果将它作为艺术品,能否挽救这种衰颓的局面?朱肇荣表示,起码在广府地区,这个可能性不强。“在广东地区却行不通,本地人几乎都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才会拿着老人生前的照片来做遗像,这种风俗习惯很难改变。”
如今,朱肇荣没有再收徒,朱家的手绘炭相手艺面临失传。“有点可惜,但也没办法,传承的事只能顺其自然。现在儿子也在电脑软件方面帮我操作,在保留手绘炭相的同时,尽量减轻工作量。”朱肇荣说。
“画得还能看吧。”说起自己的画,72岁的周强很谦虚,退休后,他便开始上老年大学,长期画大写意花鸟,现如今对于自己未来的创作,他也有了不同的想法,“以前画的都是山水大写意,画了13年,我现在就想画画我们的老石桥。”当得知江淮微公益长期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平台时,老先生连忙表示要捐两幅画作,“画得不好,可也画了13年了,你们义卖应该能捐些钱。”
擦笔画,也叫炭精画,是民国初年起源于上海的民间绘画艺术。它以炭精粉为基本绘画原料,以毛笔和纸卷自制的“擦笔”、 棉签、橡皮等为绘画工具,在纸或瓷板上绘制黑白图画;要是再辅以水彩颜料,就可以画成彩绘了。擦笔画的题材广泛,不仅可以用来绘制人物肖像,而且可以用来画广告招贴画、山水画、花鸟画等。擦笔画起源于民国初年的郑曼陀(1888~1961)。曼陀原名达,字菊如,由原籍安徽歙县的养父抚养成人。早年曾师从一位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,后到杭州的二我轩照相馆工作,专门从事人像写真。他把中国传统的人物画技法与西洋画、水彩画技法结合起来,经过长期实践探索,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画法——擦笔水彩法。先用灰黑色炭精粉作明暗层次,再加上水彩画的淡彩,所以他画的时装仕女,面部立体感强,色彩淡雅宜人,肌肤细腻柔和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画人物画传神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这“阿堵”中。曼陀深谙这个道理,他创作的人物画尤其在点睛上下工夫。他所画的人物,眉目传情,使观画者与画中人的视线接触时,产生“眼睛能跟人跑”的效果,一时声名鹊起,成为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广告、月份牌画家。
“炭”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个字,见于古代字书、后汉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中。《说文》(大徐本)上说:“炭,烧木余也。”炭就是烧木所余之物,即现在的木炭。《说文》的另一种版本(小徐本)中 则称:“炭,烧木未灰也。”炭就是烧木而未灰化之物,说得更为科学准确。《周礼、月令》上也说:“草木黄落,乃伐薪为炭”,即到了秋天,把树木砍伐下来烧 成炭。这句话也是一个佐证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名篇《卖炭翁》的第一句:“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”明白指出炭是由薪材烧成的。
我国古代,炭就是木炭,无可置疑。这个字,后来又孳生了很多转义,如“炭,火也”(《玉篇》);“炭,墨也”(《孟子》,公孙丑上,注);汉代还有以炭为姓的人(《西京杂记》)等 等。但最为重要的一个转义是,炭也指煤炭,如《正字通》:“炭、石炭,今西北所烧之煤。”现在日本人仍把煤叫做石炭,发音也和汉语基本相同,这显然是古汉 语的遗迹。自古以来,炭是一个常用的字,出现了很多有关的名词、成语和典故,如“炭妇羞”、“抱炭希凉”、“吞炭为哑”、“握炭流汤”、“生灵涂炭”、 “炭场”、“炭皮”等等。白居易的名作《卖炭翁》,更是家喻户晓,在短短的一百多 字的诗歌中,一共用了七个炭字。炭字出现频率之高,令人惊异。由此可见, 不管是天然的炭,还是人造的炭,在我国一直是用不带石旁的炭来命名的,这种用法,至少已有2000年的历史。目前,我国拥有500万职工的煤炭部、一直用这个炭字,用煤炼成的焦,也一直叫“焦炭”,也用这个炭字,绝不加石旁。有的同志认为,带石旁的‘碳’,像石头一样是指天然生成的、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炭质物质。过去我也相信这一说法。这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。
前清光绪二年(1876)在上海开办的格致书院是我国第一所工科大学。该院在成立之初,即创办木刻线装、用文言撰写的《格致汇编》月刊。该刊四年后停刊,停刊八年之后又复刊,改为季刊。这恐怕是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最早的一份期刊。《格致汇编》第四卷第十一期(光绪七年、1881)、第一及第二页上,在连载的《格致释器》栏内,有几段关于炭素材料的记载,并附图多幅,现摘录一段如下:
“作锅代炭,一种为镕化物质之用:作锅之料,以木炭细粉十分,米粉半分,水八分,先将米粉在水内沸之成浆,次加炭粉成膏。二种为矿内提出金、银、铅等用锅料,以木炭细粉九分,水略八分,次加硼砂与钠养炭养二化之,再加米粉成浆,后添炭粉成膏。造锅法,以模压成之。”
上文中所说的“锅”即现在的炭质坩锅,“钠养炭养二”即碳酸钠。同一页上还附有“炭锅”和压制炭锅的模型的图(原文七O九图及七O六图),另外在有一幅图(七一一图),图形为一空心的厚壁圆柱,正文中对这一图的说明为:“为作圆柱形炭块之模,以黄杨木为之。”
原文对七O九图的说明为:“为吹火筒工内,化分求数所需之小炭锅”。此处“吹火筒工”即现在的炉前化验工,“化分求数”即现在的定量化学分析。在以上所引文字中出现的“木炭”、“炭粉”、“炭锅”、“炭块”等,正是现在一部分炭素材料的原始刍形。值得注意、所有炭字都没有加石旁。
从以上的论述,可以肯定地说:从古自今,直到带石旁的“碳”出现之前,我国一直用不带石旁的“炭”来作为炭素材料的名称。
这座一江两岸的城市拥有672375人,生生死死逐日上演。跨江大桥之上散落在地的破旧摩托车,北江边上偶尔被人发现的浮尸,医院内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。据统计,清城区2015年死亡3829人,平均每天火化遗体11具,多时接近20具。
画遗像的姐妹:24年画像一万多幅
南门街巷子内,挂着写有“画像”二字的炭画,这是谭小琼的档口。谭小琼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在此摆摊24年,这些年来,每人每年约画300幅画像,共画像7200幅,两人共画11400多幅,其中遗像占据80%。
她们离悲伤很近,重现逝去之人的容颜,留住在世之人的回忆。
来画像的多数为老人
上个月中旬,一位身材高大、打扮得体、戴着眼镜、气质儒雅的四川老人来清远参加婚宴,闲逛时看到“画像”的档口,便想着给他的父母画张像。因为老人要赶路,凭着一张年代久远的大合照,姐妹俩合力,花了一天,把两个老人的合照画完。经过几次修改,老人把照片发给身在海南的侄子,确认“神似”后,又让她多画一张,给侄子寄去。
父母的形象重现,老人很是感激。末了,还请谭小琼吃饭。这令她印象深刻:这是第一个请她吃饭的顾客。
像四川老人一样,为父母“补张照片”的老人不在少数,“算是一种心理安慰,寻求心灵的慰藉。”
来让她们画像最多的还是老人。也有老人特意在画像后面加句留言: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老人感叹,年轻时打拼没有报答父母,只能现在缅怀一下。
也有凭借后代模样为亲人画像。中年男人要为抗日烈士的爷爷画相,家中只有他最像爷爷,于是将自己照片作为参考。
“有不少老人没有照片,或照片掉色、模糊不清。只能靠他们的孩子描述,或者找到最像他的人照片参考。”潭小琼说,只能从描述中理解,也要多番拼凑、修改。
见证那些生与死的故事
画像本是谭小琼父亲的爱好,长大后跟随父亲学习,成为姐妹俩的谋生之道。20多年来,帮各种人画像,也留住过一场场生命的记忆。
一名70多岁的妇女,拿着老公年轻时的照片,请求画合影。谭小琼便把妇女处理得年轻一些,画中男人画得年长一些。对于要画合影的,谭小琼还是会多嘴提醒一句,“还是建议在生的和过世的分开画再拼在一起,或者再画一张单人照。”
画遗像的除了老人,还有意外死亡的小孩子。谭小琼说,最小画过7岁的小孩,这样年轻的孩子有三个。一个是车祸死亡、两个是溺死的,照片多由帮忙处理后事的亲友带来,只有这样身份的人过来,跟谭小琼聊上两句,她才会知道背后的故事。
她也极少过问像中之人的事情。“不问死亡,不问缘由,只管画画。”有一些顾客看到画照片流眼泪,遇到一些心情特别沉重的顾客,更是不敢多言。
曾经遇到过伤心至极的老妇来给两个儿子画像,谭小琼只开口问了一句“这是你的儿子吗?”老妇便大哭起来。不会安慰人的谭小琼手足无措,幸亏旁人不停安慰,她才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,一个尚未结婚,一个儿子6岁,或因病、意外而去世,老人独自一人带着孙子过活。
年轻人找“代笔”
也有60多岁两夫妻为自己准备遗像,她也不问原因。大多数人提的要求是画得慈祥、包容一些。如果露齿严重的、皱纹多,还会美化修饰一下。遇到赶时间的,两姐妹合力,快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完工一幅。
除了老人、名人,谭小琼画的还有一些娱乐明星。一些学美术的小男生,想送给自己喜欢的女生,功力不够,就来找到谭小琼“代笔”,还嘱咐“不要画得像遗照哦。”所以她的手机上保存着画过的TFBOY、花千骨的画像,还有年轻小女孩的画像,画完,便给小男生寄过去。
虽然现在的影印技术已经很先进,但谭小琼认为,炭画这样的民间艺术更具有艺术感和时代感。她说,炭画最大的优点是长时间不褪色,保管得好越放越好看。“炭画保存时间长,人工操作,比起冲印技术,无论是成像还是保存都更胜一筹。”
“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放炭相在家里,一般放在祠堂或旧房子。”因此生意比以前差了些。谭小琼回忆道,八十年代时,南门街不少人作画,形成“三足鼎立”的画面。而如今只剩下她和妹妹在作画了。
面对生老病死的众多“人像”,看到年轻人的遗像她也会感到惋惜,谭小琼感悟:人是按一个个算的,并不是按年轻算的,身体健康就最重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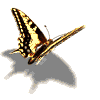
您知道中国炭精画吗?中国炭精画,炭精画像新概念!又称“炭精画”“炭画”,以羊毫笔为工具,炭精粉为颜料,揉擦于质地紧密而强韧的绘图纸上,比摄影照片还要栩栩传神,适合绘制人物、花鸟、山水。“炭精画像”发祥于19世纪九十年代,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细腻自然,奇妙无比!一经装框,永不褪色……作为国粹不言自明!广泛受到各地人民大众的喜爱,令投资者、收藏家热捧。各地新闻媒体称“中国炭精画正走进千家万户”。
天下炭友是一家!炭精画官方QQ群(群号:330233164)欢迎加入。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欢迎您回家!各地素描达人、画像从业者、美术收藏家,均在欢迎之列!也欢迎有志者创建炭精画(城市)俱乐部”!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长期选拔分部主任,为主任颁发聘书,开通官方互动窗口,发放工作经费。成绩突出者吸收为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成员。
组长:张智华
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
——————
炭致广大,
精微传神!
画美人生,
像形铸魂!
——————
奇妙的中国炭精画
享誉全球的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,聘请中国教育学会(CSE)会员、湖北省书画研究会(HBDPRI)会员、方圆格练字创始人、炭精画像新概念“中国炭精画”提出者张智华老师出任组长。张智华老师为抢救和传承这门濒临失传的民间美术,曾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利用课外时间拜访多地画师,还参加了贵州省毕节炭精画像馆杨君明馆长亲授课程。除了语文教学与研究之外,张智华老师为父老乡亲绘制炭精画像近万张,提出了炭精画像新概念“中国炭精画”。时人以得到他绘制的炭精画为荣。1996年8月,《奇妙的中国炭精画》印行,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。“中国炭精画”概括地来说有两点,一是抓住了“中国”(文化),另一个是抓住了“炭精画”,名副其实。2010年4月,炭精画域名(tanjinghua.com)注册成功。2013年7月9日,年逾古稀的“毕节一绝”毕节炭精画创始人杨君明馆长来到宜昌,指导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工作,饱览美丽而神奇的三峡风光;师生真情,把杯畅饮,短短半月,意犹未尽……宜昌——这座“全国文明城市”,给老馆长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。
Powered By www.tanjinghua.com ,Theme By 中国炭精画世界 Please respect the author to keep this link。
www.tanjinghua.com 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 
中国炭精画总课题组 | 资讯爆料QQ:791541679 | 关于我们 | 内容说明 | 作者申请 |